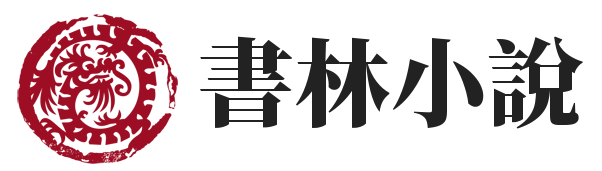第3章
魏洵湊在我耳邊低聲說話,清淺的呼吸噴在我脖頸間,酥酥麻麻,泛著痒。
我頗有些不自在,但念及身後的舊傷無法獨自一人騎馬,便任由他去了。
初春的風帶著些許寒意,吹得我縮了下脖子,頰邊的耳墜晃晃蕩蕩,叮當作響。
裴玄撥開弓箭手,一步一步走到城牆最前頭。
冷冷開口;「放了阿衡。」
不知是否是我的錯覺,魏洵似乎極輕易地笑了一聲。
然後,在眾目睽睽之下,他抱著我翻身下馬。
動作幹淨利落,半分顛簸都沒有。
Advertisement
「是這樣放嗎?」
魏軍哄堂大笑,裴玄臉色鐵青。
城樓上的士兵將弓繃得很緊,魏洵卻挑挑眉,絲毫不懼。
魏洵勢強,手握十數萬兵馬,不久前剛取勝於東吳,自然不會畏懼一個不久前才劃地稱王的楚地。
兩軍劍拔弩張。
片刻後,還是裴玄先低了頭。
城門開出一條小縫,有使者出來奉上籍冊。
上面蓋著楚地的皇章,聲明彭城與虞城兩座城池劃分給魏地。
魏洵看也未看,反而微微俯身,替我整理領口的鳳毛。
「你若是不願回去,本侯拿了籍冊便立時攻城。」
我笑笑:「君侯有君子大義,又怎麼會做出此等出爾反爾的事?」
魏洵神色坦然:「為將者,應當明白兵不厭詐的道理。」
「妾還有旁的事情要做,還望君侯放手。」
我微微搖頭,魏洵輕嘆一聲。
似惋惜,似釋然。
我想,他大抵是在惋惜失去了一個好軍師。
從前未出嫁時,父親便說過我有將帥之才。
隻可惜,是個女兒身,否則在這亂世之中,應當有一番作為。
一陣寒風襲來,領口處的鳳毛被吹得立起,似蘆葦般搖擺。
魏洵翻身上馬,微微吐出一口濁氣。
輕蔑地看了裴玄最後一眼:「日後若是再遇上追兵,還是不要將妻室趕下馬車的好,否則本侯若是再撿到,十座城池也不換。」
大軍頃刻間便退去,隻餘漫天塵沙。
我撫了撫衣角的褶皺,然後目不斜視地走進了青州城。
9
我本以為裴玄會為難我。
畢竟方才魏洵當著眾人的面叫他難堪,以他往日的脾性,定然是會要宣泄一番的。
可他並沒有。
他命人備下最好的軟榻,和最暖的地龍,甚至房間裡,還備下了藥浴。
我在婢女的服侍下梳洗完畢後,裴玄才姍姍來遲。
他低垂眼睫,目光落到我肚子上。
「幾個月了?」
魏軍糧草豐厚,時不時獵得野雞野兔野豬時,魏洵也會派人給我送來一些。
在軍中養傷的數月裡,我不僅沒瘦,反而豐盈了不少,打眼瞧著,還真有幾分孕相。
於是,我輕撫小腹,答道:「三個月。」
我被魏軍俘虜將近兩月,三個月前,正是我陪裴玄出徵的時候。
裴玄原本極少與我親近。
可那時程錦上帶著一雙兒女來探軍,整日裡同裴臨柔情蜜意。
裴玄嫉妒得發瘋,夜裡,他便上了我的床榻。
算起來,正是那次有的。
不多不少,正好三個月。
瑩瑩燭光下,裴玄的目光柔和了幾分。
他言語中,甚至罕見地帶了幾分歉意。
「那日……是我魯莽了,可兄長戰S,長嫂和他的一雙兒女我不能不顧,阿衡,莫要怪我。」
他這話說得冠冕堂皇,仿佛若是我不能理解便是不仁不義一般。
若是從前,我定然會同他辯駁一番。
可如今……
沒這個必要了。
我隻笑笑:「事出突然,怪不得你,再說我如今不是回來了嗎?」
裴玄點點頭,像是釋然了幾分。
第二日一早,卻請來醫女,說要幫我瞧瞧舊傷。
哪裡是要瞧什麼舊傷,分明就是要驗一驗我腹中的孩子。
我心中了然,並不在意。
白芷早就給過我抑制脈相的藥,隻要服下,脈相便能圓潤如珠。
直到那醫女篤定地告訴裴玄,我的確是有孕三月有餘,他才徹底放了心。
第二日,大軍即刻啟程回楚地。
說起來青州離楚地皇宮並不十分遠,不過兩百裡的腳程。
若是騎快馬三個時辰就能抵達,就算是坐馬車也就一兩日的工夫。
可裴玄硬生生拖出三日來。
一路上,他殷勤得不像話。
又是端茶送水,又是替我捶肩捏背。
甚至連我從前愛吃的酸棗糕,他都讓人尋了來。
青州不產酸棗,那做糕的阿婆也離世多年,不知他是費了怎樣一番功夫才尋來。
可我卻不要了。
「妾不愛吃酸。」
「可你從前明明最愛……」
我無聲地笑了笑,掀開車簾,刺骨的寒風吹得人心中一凜,卻叫人更加清醒。
「殿下也會說從前了。
「從前妾的確愛吃酸,可殿下說楚地口味嗜甜,是以每每糕餅飯食之上,都對嫂嫂諸般遷就。
「跟著殿下的這許多年,妾早就不愛吃酸了。」
鬥轉星移,物是人非。
如今糕和人,都隻會叫我作嘔。
裴玄神色一暗,拳頭握了又松。
「阿衡,從前諸般種種都是我的錯,往後,我一定會竭盡全力彌補你的。」
我擔憂地撫上小腹:「可若是有人容不下我和孩子呢?」
「不會的。
「錦上性子謙和溫婉,絕不會善妒至此。」
裴玄目光堅定,神色懇切。
我垂首不語。
因為他很快就會知道。
楚地皇宮裡,容不下我的。
可不止程錦上一個。
10
第三日清晨,大軍抵達了楚地。
剛進皇宮,裴玄便被迫卸了甲,我與他一同被押送到太極殿。
御座上的楚王臉色陰沉得幾乎要滴出水來。
見裴玄進來,揚手便扔了個茶盞:「逆子!竟為了個女人,去偷朕的玉璽,還割讓了兩座城池給魏洵,楚地的臉都讓你丟盡了!」
我此刻才明白,為何楚王會答應割讓兩座城池來換回我。
原來,那玉璽竟是裴玄偷的。
鮮紅的血順著額角蜿蜒而下,裴玄跪伏在地。
「是兒臣的錯,可阿衡是兒臣的發妻,若是任由魏洵把持,豈非有辱皇室臉面?」
楚王冷笑一聲:「不過是個鄉野出身的婦人,跟著你享了幾年的福,你還真將她當作結發妻子了?
「且她既被魏軍所俘,便應該以S保節,而不是苟活到現在!」
殿中的男人紛紛點頭。
他們有的是裴玄的王叔,有的是裴玄的族弟。
可唯一相同的是,他們都有數不清的姬妾,就連御座上那位年過花甲的楚王,也有三宮六院。
若是論起守節,他們合該在我前頭自裁。
可令人可悲的是,他們竟論起了我的貞潔。
有內侍上前奉上一杯鸩酒,楚王橫了我一眼:「若是乖覺,此刻自裁,還能保全江家顏面。」
裴玄擋在我身前:「父王,阿衡她有了身孕。
「那是我的孩子。」
楚王嗤笑一聲:「那又如何?
「她在敵營數月,且先不說這孩子是不是你的,即便是你的,有一個名節不保的生母,他出身能高貴到哪裡去?
「楚地貌美的貴女多的是,日後再生十個八個也不是什麼難事,你莫要犯渾。」
那內侍又上前一步,將酒杯奉到我眼前,卻被裴玄一腳踹開。
他眼底有怒意翻騰:「父親該曉得,如今大哥已S,我或許能決定自己的兒子有幾個。
「可您的兒子,隻有我一個。」
楚王暴怒,剛站起身,便眩暈著又坐了回去。
他的確老了。
再看殿中,除了裴玄,還有一眾虎視眈眈的王族親眷。
他們都盯著御座上的位置。
兩相比較之下,血脈親情似乎比氏族名聲要重要些。
於是,楚王妥協了。
「罷了,你若喜歡,便隨你了。」
裴玄將我安置在了長秋宮。
我隨他出徵前,裴家還未曾畫地稱王,這是我頭一次住這麼大的宮殿。
裴玄剛回楚地,政務繁忙,並沒有多少工夫來打攪我。
裴家氏族的其他貴女本就瞧不上我,如今更是鄙夷。
我一個人守著偌大的宮殿百無聊賴,闲得發慌。
第二日,便去尋了程錦上。
11
程錦上帶著一雙兒女住在朝露宮。
裴玄他哥裴臨戰S,如今已然封了賢王,程錦上便作為賢王遺孀暫居在朝露宮。
幾月不見,兩個孩子又長大了些。
我剛一進門,他們便撲了過來,險些將我撞倒在地。
程錦上慌慌張張地將他們拉開,有些害怕:「弟妹沒事吧?」
我這才想起來她是在問我的肚子,連忙站起身。
「無事。」
她長舒了一口氣,將兩個孩子託付給乳母後,才轉身給我倒了茶。
見我不喝,她幾乎要將手中的絲帕絞碎。
「阿衡,那日……那日原是我拖累了你們,若不是我,你也不會……」
她欲言又止,說到最後竟落了淚。
美人落淚,自是如梨花帶雨,香蘭泣露般哀絕。
「這不是你的錯,將我趕下馬車的,是裴玄,不是你。」
她嘆了口氣,「你不曉得,那日小叔有多悔,事後他曾派人去尋過你,情急之下甚至還想自己親自去找。
「說起來,他待你的情意並不淺,阿衡,如今你既平安回來,又有了身孕,合該是將這日子好好過下去的。」
我定定地看著她,那雙溫潤的眼裡竟找不出一絲狡詐。
日頭穿過珠簾照了進來,落到程錦上臉上,越發顯得她纖白溫婉。
我的夫君惦記她多年,也將我與她作比多年。
我被貶進塵埃裡一文不值,她卻被記掛在心上明月高懸。
我原本是應該恨她的。
可我卻做不到。
大抵是因為那些被裴玄厭棄趕出營帳的日子裡,她隨手奉上的一碗熱粥。
又或是我落馬傷腿後,她細心為我換藥的幾個日夜。
那些細碎的東西勾勾畫畫,終是描繪成了一個溫婉善良的程錦上。
可她好她的,並非就能說明我不好。
我們都是頂頂好的女娘,唯一的汙點,便是裴玄。
我端起茶盞喝了一口:「嫂嫂,大哥從前待你好嗎?」
程錦上彎唇點了點頭,極羞澀的少女模樣。
我又問:「比裴玄待你還好嗎?」
她蹙眉搖了搖頭:「我與小叔從前的婚事,不過是年少時的玩笑,當不得真。
「可阿臨不一樣,阿臨他為人溫厚和順,會替我描眉上妝,替我挑選羅裳,亦會在夏日裡替我採上最豔麗的芙蕖,如今卻……」
說到最後,她眉眼染上了幾分憂傷。
那樣的謙謙君子,最終卻英年早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