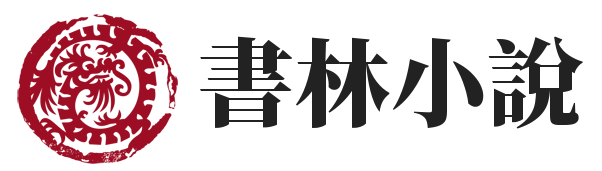第2章
「好S不如賴活著,妾就算與裴玄再不睦,也不會蠢到在這種時候自尋S路。」
魏洵不說話,目光落到我懸在榻邊的小腿上。
方才有醫女上過藥,紗布與褻褲之間露出一小片皙白的皮膚,上面遍布紅痕與傷口。
那是蒺藜刺過的痕跡。
他眸光微微驟縮,聲音不自然地有些艱澀。
「你打算如何做?」
我微微坐直身子,又攏了攏鬢發,努力讓自己看起來得體些。
然後,拉開了衣襟。
Advertisement
僕婦與醫女漲紅了臉,立馬退了出去。
魏洵驟然起身,有些惱怒地冷笑:「夫人若是想以此事激怒裴玄,本侯覺著大可不必。」
「君侯多慮了。」
我搖頭輕嘆一聲,將衣襟拉得更大了些。
然後,從小衣的夾袋裡取出了那塊玉珏。
「我與裴玄成婚時,他尚未起勢,裴父為了讓我父親答允這樁婚事,便尋匠人打了兩塊鴛鴦玉珏,允諾日後若是裴家起勢,我江家女便能憑此玉珏號令萬軍。
「如今裴家在楚地自封為王,這玉珏,也到了起作用的時候了。」
魏洵嗤笑:「裴家人刻薄寡恩,夫人應當早就見識過了,如今竟還盼望著這昔日的玉珏,能號令如今的楚軍?」
「有沒有用,君侯試試不就知道了?」
魏洵移開目光,耳廓緋紅。
接過那枚玉珏時,手指微微一頓,像是被餘溫燙到了一般。
然後,掀開帳帷走了出去。
我吐出一口濁氣。
明白自己總算是多了一分生的指望。
5
魏洵並未說過要如何發落我,我便順理成章地留在了軍中。
軍中的僕婦們闲來無事,便會坐在樹下分揀草藥。
帳簾微卷,寒風將她們的議論聲吹進帳內。
「當真是個不知廉恥的狐媚子,那日我們都在呢,她便大咧咧地扯開領子要勾引君侯。」
「還有這事兒?」
「當然了,否則君侯怎麼失了心智一般,非要力排眾議留下這個毫無用處的女人?想來是她伺候人的手段實在不一般,這才……」
幾人對視一眼,面露鄙夷。
替我上藥的醫女手指一頓,小心翼翼地看我的神色,大抵是怕我惱怒,抑或撒潑。
可我都沒有。
從前在楚軍營帳中時,我聽過的闲話,比這多得多,也比這惡毒得多。
我陪裴玄出徵,為他洗手作羹湯,他們說我出身鄉野,上不得臺面。
兩軍交戰,我奔赴千裡拼S送軍報,不慎摔斷了腿,他們說我延誤軍機,是楚地的罪人。
總而言之,言而總之。
這一切的一切,都隻是因為,我是亭長江山的女兒,雖從前掌邑千戶,但如今在是皇子的裴玄面前,已經不夠看了。
從前的諸般折辱,和如今的千般磋磨,都是拜裴玄所賜。
所以,我都會記在他身上。
上完藥,我又要了一碗肉羹,並一碟幹糧。
剛吃完,準備小憩一會兒,魏洵便來了。
他一身玄色裘衣,領口處的鳳毛沾著幾粒殘雪,襯得人格外清冷幾分。
「你倒是能吃能睡,像是在家一般。」
我笑了笑:「人生在世,須有定數,事多而食少,不是長壽之相。
「總不能因為被夫君拋棄了,便尋S覓活吧?再者,我若是不多活兩天,君侯兵臨楚地時,又該如何號令萬軍?」
魏洵冷笑一聲,抖落了肩上殘雪。
「本侯從未指望過你那所謂的玉珏能號令萬軍。」
那的確是我胡謅的。
於是歪頭質詢:「那是?」
既然不信,又為何要留我一命?
「你可曉得,裴玄回到楚地後,前後派了近百人去西華山尋你。
「三日三夜,無一刻停歇。」
他深深看了我一眼。
「既如此,就說明,你於裴玄而言並非棄子,而是……」他頓了頓。
「情急之下不慎遺落,卻始終無法尋回的珍寶。」
聽完最後兩個字,我忍不住笑出了聲。
我籌謀來籌謀去,為了保命連那塊玉珏都拿了出來。
到最後,竟是自己成了那塊最有用的籌碼。
「君侯既覺得妾如此重要,那如今是要拿我換城池?」
魏洵的目光落到我身上,深淵一般叫人捉摸不透。
「若隻是如此,豈不是暴殄天物?」
我哈哈一笑:「若君侯覺著妾那日許下的承諾還能相信,便請君侯給裴玄書信一封。」
「寫什麼?」
「就說,妾孕吐得厲害,想吃楚地的酸棗糕了。」
6
風雪初歇,萬籟俱寂。
殿中地龍燒得很暖,還燃著安神香,裴玄卻罕見地做了夢。
他夢見十七歲那年,裴家敗落,原本同程家定下的姻親也被毀去。
他發誓要另闖出一番天地,好叫程家後悔,於是孤身一人前往青州闖蕩。
也是這樣一個冬日,他行路數十天,身上的銀兩早就已經花光,渾身上下連一件完整的衣衫都沒有。
為了果腹,他摒棄臉面,想要偷些吃食,卻在入戶竊糧時,被抓了個正著。
他本以為自己會被押送府衙,可那戶人家卻並未為難他,反而將他請進正堂飽餐一頓,還給了他一身御寒的衣物。
甚至,還將自己唯一的女兒許配給他,又借自己亭長的身份替他奔走招安。
後來,裴玄亂世起家,逐漸成為楚地霸主。
程家這才曉得自己看走了眼,可裴玄已經娶親,便隻能將從前與裴玄定親的程錦上許配給了裴玄的大哥。
無數個輾轉難眠的夜,裴玄都在後悔。
既悔自己不該聽從江亭長的話,娶了江衡。
又悔自己要顧及裴氏一族的臉面,不能休了江衡另娶。
樁樁件件,都帶了江衡的名字,讓裴玄不得不將這些惱意傾注在她身上。
所以,婚後數年,他從未給過她什麼好臉色。
夢裡,江衡端了盞茶進來,放到案桌上。
「妾新做了茶,殿下嘗嘗吧。」
像烹茶這樣的事,錦上做自然是紅袖添香,溫婉柔情。
可若是換了江衡,那便是東施效顰,滑稽不堪。
她本就出身鄉野,上不得臺面。
裴玄看著那清澈的茶湯,皺了眉:「出去吧,無事不要進來。」
江衡似乎愣了一瞬,隨後掀帳出去了。
裴玄莫名心中有些怪異,頓筆抬頭,順著掀開一角的帳簾望出去,卻並沒有看見江衡的背影。
而是白茫茫的雪幕。
原來是那一天。
馬車疾速前進著,四周都是魏軍射出的冷箭。
然後就是被自己推下馬車的江衡,她在地上滾了好幾圈,然後勉力站起。
泥濘不堪的雪道中,她孤零零地站著。
叫裴玄無端想起三年前,鹿鳴關一戰中,所有人都被圍困峽谷之內。
是她孤身一人,奔襲千裡送去軍報,方才解了困境。
援軍解困後,她也是這樣孤零零地站在帳外,聽那些楚地的族老數落她。
他們斥責她行事不穩,半路竟落了馬,以至於延誤軍機,否則軍中將士損傷不會這麼慘重。
那時,他忙著寬解剛剛失去丈夫的錦上,顧不上她。
隻記得,她微微躬身,站在風雪裡,像極了青州被風雪壓彎的翠竹。
後來,他才曉得,她從馬上落下來,摔傷了腿。
隻可惜,他知道這一切的時候,已經回到楚地了。
否則,他也不會將她趕下馬車。
應當是不會的吧?
除了將她趕下馬車,應當還是有別的法子的吧?
西華山的寒風吹得人心中一凜。
裴玄頭痛欲裂,自夢中驚醒。
恍然間發覺自己是在楚地的皇宮中,他竟有些失望。
有宮娥過來稟告:「殿下,春華殿來人說兩位小皇孫發了高熱,大皇子妃急得不行呢。」
裴玄扶額,不說話。
從前若是錦上和孩子有什麼事,他必定是關切至極的,可如今,卻莫名有些煩躁。
「西華山那邊,可有消息了?」
內侍輕輕搖頭:「並沒有。」
也是。
西華山陰寒險峻,便是尋常男子入內,都有可能遇險,莫說是受傷的江衡了。
裴玄轉頭,盯著搖曳的燭火發呆。
喉頭莫名有些艱澀。
直到,冷風卷起珠簾,有人疾步走了進來。
雙手呈上一封書信——
「殿下,有皇子妃的消息了!」
裴玄大喜過望,站起身時,險些絆倒了燭臺。
「果真?」
「千真萬確,魏侯來了書信。」
「信中說……說皇子妃她有了身孕。」
「啪」的一聲,將落未落的燭臺掉在了地上。
摔得粉碎。
7
半月後,楚地送來了回信。
信中說,他們願意以兩座城池為代價,換我重回楚地。
魏洵派人將書信送來給我看時,我正在窗邊吃烤兔。
服侍我的醫女白芷十分擔憂:「夫人未曾在信中說明自己有孕的月數,難道就不怕裴玄心生疑竇嗎?」
這便是魏洵的高明之處了。
我被魏軍俘虜數月,如今驟然有了身孕,他卻不曾明言這孩子到底是誰的,反倒叫裴玄不敢輕舉妄動。
我渾不在意地搖搖頭:「反正我如今在魏地,裴玄再惱怒,還能S了我不成?」
白芷欲言又止:「可……」
我曉得她在擔憂什麼。
不過是因為,魏洵已經同裴玄商定好,要拿我換颍都與彭城兩座城池。
三日後兩軍便會同時抵達青州,而我便要回到楚地。
楚地雖民風開化,但裴家早已自封為王,我如今是王室的女人,自然容不得半分玷汙。
裴玄之所以願意換我,大抵也是為了楚家的名聲和臉面。
一個被敵軍俘虜,名節又不清不楚的女子,下場不會好到哪裡去。
因此,這幾日,那些從前風言風語的僕婦都安分了許多。
連撿草藥時,口中議論的也都是:「一個女人,被敵軍所俘,能活到今日實在是不容易,若是要回去,嘖嘖……」
「聽說楚地刑罰眾多,尤其是針對女子的,那她……」
人人都為我即將了結的後半生惋惜。
可我卻曉得,此行於我而言,名節是最不重要的東西。
我啃完最後一口兔肉,將腿骨扔到樹下。
樹葉窸窣間,似乎閃過一片玄色的衣角。
我揉了揉眼,再去看時。
才看清,不過是一隻展翅的春蟬罷了。
8
三日後,魏軍如約抵達青州。
時隔數年,我再次站在青州城下,隻覺得恍如隔世。
恍惚間又想起自己木著一張臉從城門出嫁,十裡紅裝直達楚地。
又仿佛看見父親舉全家之力助裴玄起勢,而後整個江家迅速沒落,自此從青州除名。
我這一生,大喜,大悲,竟都是因為同一個人。
而此刻,裴玄就站在城牆之上。
他站在數以萬計的弓箭手身後,目光從我臉上,下滑到我腰間,最後落到了魏洵裹挾著我的那隻臂膀上。
一雙眼,陰沉得幾乎要滴出水來。
我微微掙扎,魏洵卻靠得更近。
他兩隻手自我腰間穿過,輕縱韁繩。
「夫人不是說,謀者,攻心為上嗎?如今怎麼反倒退縮了?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