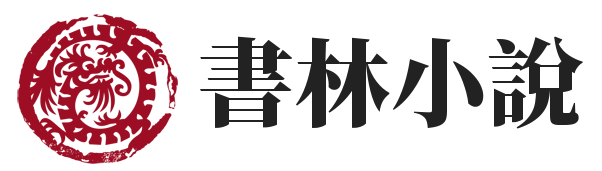第4章
怎能不令人惋惜?
我捏著水杯,看著水波晃蕩。
「我聽那日的參將說,原本大哥是能全身而退的,隻是那匹戰馬不知為何出了差錯,崴了腳,才叫大哥殒命。」
「你是說……」
我搖搖頭:「也許是上牧官弄錯了也不一定。」
可我們都明白,絕無這個可能。
戰馬都是從楚地統一採買的,絕無差錯。
唯一能有差錯的,便是人為了。
Advertisement
程錦上一張臉慢慢變得慘白,眼淚大顆大顆地砸下。
「是我錯了……是我錯了,若是我未曾嫁給阿臨,他也不會……」
「是裴玄的錯。」
即便她沒有嫁給裴臨,以裴玄陰鸷瘋癲的性子,也一定會糾纏她畢生。
或許對於這種瘋狗而言,得不到的,就是最好的。
程錦上慢慢站起身,像是在笑,又像是在哭。
我撿起地上那張被指甲勾花的絲帕,替她擦了擦淚。
平靜道:「始作俑者,其無後乎。
「嫂嫂,不急的。」
12
第二日,程錦上便帶了羹湯過來,說是特地給裴玄做的。
她輕擺雲袖,像是一朵輕盈的雲般飄進了內殿。
好久好久,都沒有出來。
夜裡內侍去收拾時,從書案下揀出了被撕碎的小衣。
我假裝不知道。
宮娥湊在廊下多嘴,她們說程錦上裝了這麼久的貞節烈女,始終不肯與二殿下親近,如今正牌皇子妃回來了,她開始惴惴不安了,所以便恢復了本性。
她們罵她狐媚下賤,亦斥她不知廉恥。
說來也怪,這些詞,從前明明都是用來形容我的。
如今程錦上略略親近裴玄些,挨罵的便成了她。
由此可見,誰與裴玄親近,便注定落不著好。
裴玄從太極殿回來時已經是深夜。
宮娥吹了燈,殿裡影影綽綽的。
他撥開層層疊疊的帳帷,坐到我床頭。
「你今日是不是聽說了些什麼?」
我嗯了一聲,裴玄嘆了口氣:「阿衡,不要恨她,她也很可憐。」
我無聲地笑了笑。
「等你平安生下孩子,我會納她為妾,但正妻之位仍舊是你的。」
裴玄目光堅定,神色懇切。
像是我初次見他時的模樣,一如既往,胸有成竹。
他篤定程錦上會甘願委身他做妾。
也篤定我繼續回到楚地做那個賢良淑德的江衡。
金銀寶和玉如意,他一個都不想放。
但好在,如今他什麼都得不到。
我摸摸肚子,程錦上告訴我,女子有孕四個月時便會顯懷。
我的時間不多了。
裴玄作為儲君,並沒有多少時間能陪著我。
他每日裡有佳人在畔紅袖添香,鮮少來看我。
長秋宮的宮娥很多,每日裡在廊下走走停停,她們或是擦地或是剪花,連最細微之處都能顧及。
卻唯獨沒有瞧見那隻總在夜幕時分飛進內殿的信鴿。
那信鴿飛飛停停,半月後,有人翻窗進來。
那人一襲玄色衣衫,輕輕巧巧地鑽進帳帷之內。
急急開口:「聽聞楚王欲S你正節,你可還好?」
我攏起松垮的褻衣:「若是君侯不這麼堂而皇之地偷香竊玉的話,妾應當是很好的。」
昏黃的豆燈將魏洵的耳廓照得發暖:「我……我沒有。」
層層疊疊的帳帷後是影影綽綽的珠簾,值夜的宮娥就睡在那裡。
我將豆燈又吹滅兩盞,問他:「東西可收到了?」
魏洵點頭。
「我方才進來時看過了,此時正是侍衛交班之際,你我若是要蒙混出宮,並不難……」
我搖頭:「我不走。」
魏洵蹙眉不解。
「當初妾是堂堂正正嫁進來的,如今要走,自然也得是堂堂正正地走。
「再者,君侯當初允諾妾的,如今還沒有實現呢。」
魏洵深深地看了我一眼,然後又鑽出帳帷,飛身越過宮牆,頃刻間便沒了蹤影。
像是那隻玄色的信鴿。
有油潤的香氣傳來,我低下頭,錦被旁不知何時多了個油紙包。
裡面,是兩隻溫熱的兔腿。
13
第二日,我發起了高熱。
原本隻是受了風寒,靜養即可。
可一碗一碗的湯藥灌下去,我依舊沒有好轉。
醫女診脈後說,我是寒氣入體太深,所以才會如此。
若是能有一株靈山的錯紅草入藥,或許能緩解一二。
寒氣是如何入體的,裴玄比我更清楚。
若不是他將我趕下馬車,我也不會落下這樣的病根。
春寒料峭,廊下的冰柱都還未曾消融。
當天夜裡,他便單槍匹馬地去了靈山。
可沒承想,草藥未曾採到,人倒是被一早埋伏好的魏洵俘虜了。
裴玄素來武藝精湛,照理說獨身一人又有快馬,是不會被輕易俘虜的。
眾人都很疑惑,唯有程錦上了然。
三日後,魏洵帶著裴玄兵臨城下。
楚王氣得急了竟一病不起,幾位王叔爭先恐後地侍疾,無一人搭理裴玄。
說來可笑,最後站在城牆之上與魏洵對峙的人,竟成了我。
千軍萬馬前,裴玄脖頸和腳踝處都戴著镣銬,衣衫褴褸,遠沒有當初我被俘虜時的恬淡愜意。
見我出來,裴玄欣喜了一瞬:「阿衡!」
我撫摸著肚子:「魏候這回想要幾座城池才肯放人?」
魏洵極輕地笑了笑:「古往今來,能換城池的都是美人,一個男人,是不值錢的。
「尤其是一個背信棄義,拋妻棄子的男人。
「既如此,便換一座吧。」
這並不是什麼苛刻的條件,裴玄幾乎瞬間就松了口氣。
可下一瞬,魏洵又說:「我隻要珺都。」
珺都,是楚地的都城。
此話一出,楚地的士兵都倒吸一口涼氣。
裴玄慌張起來,他顫著腳跑了兩步,卻被鎖鏈拽倒在地。
「父王,救我!」
回應他的,是一支自太極殿眺高處射出的冷箭。
那支箭擦著他的鬢角而過,惡狠狠地插進沙地裡。
這就是裴氏一族給出的答復。
魏洵十分可惜的模樣:「好不容易抓到個俘虜,沒想到,竟是個沒用的貨色。
「楚地竟不願贖你,本侯應當怎麼處置你呢?二殿下不妨與本侯說說,楚地從前是怎麼處置俘虜的?」
裴玄肝膽俱裂。
從前戰場上交鋒時,他們不是沒俘獲過魏軍的人。
裴玄行事殘忍狠辣,所俘的士兵大都成了練劍練槍的活靶子。
如今落到自己身上,果真是報應不爽。
「君侯心存善念,不忍S戮,那便不妨便將他丟入西華山吧。
「殿下性子堅韌,想必無論如何都會有活下來的機會。
「此般,也能成全君侯的君子大義。」
裴玄的眼神從不解,轉變成錯愕,最終變成一片恍然。
就是在這一刻,他明白了。
從我重新回到他身邊的那一刻開始,這一切都是報復。
唯一的目的隻有一個——
從前我受過的磋磨,他都要受一遍。
這才叫報應不爽,不是嗎?
14
魏洵退兵了。
他讓人打折了裴玄的左腿,又依葫蘆畫瓢將他的脊梁折斷一截,才將他丟入西華山。
收到魏洵的書信時,楚王已然立儲。
他S前將王位傳給了程錦上的兒子裴松,那是他唯一信任血脈的皇孫。
我也不必再裝了,卸了枕頭的第二日,我便提著長槍,將裴氏一族的族老S了個幹淨。
不為旁的,隻因我翻閱了楚王的往日的密信後,得知從前江家眾人的S因。
我阿爹阿叔,並不是S在仇家之手,而是裴家眾人手裡。
那時楚王已然畫地稱王,裴玄雖厭棄我卻並未讓我下堂。
他們便擔心將來我若是做了王後,江家眾人有外戚幹政之嫌, 再者,從前裴家落魄時, 江家眾人皆是看在眼裡的。
所以, 就為了那一星半點的猜疑和臉面,江家滿門被滅。
他們S前眼睛仍舊瞪得老大,似乎不敢相信, 向來唯唯諾諾恭謹溫順的江家女, 竟然還熟習武藝。
可我早就說過的。
是他們不信。
他們不信我配得上做裴玄的妻室, 也不信我能憑借卑賤的出身當好一國之母。
但好在, 最後這些偏執與輕蔑,最終SS了他們自己。
程錦上平靜地幫我收拾了殘局, 那些屍體都被丟去了亂葬崗。
替我擦拭手上的鮮血時,她面不改色, 一句都沒有問。
就像是當初, 我也沒有問過她送給裴玄的那些羹湯裡,到底是什麼。
從始至終,我們的目的都是一樣的。
沒幾天, 便傳來裴玄身S的消息。
他拖著一條殘腿, 被猛虎吞吃入腹, 連半塊殘肢都未曾留下。
隻留下半塊帶血的鴛鴦佩。
楚王出殯的第三日, 裴松登基稱帝。
程錦上作為太後, 親手寫下退位信箋,讓宮人誊抄千份。
那一日恰巧是清明, 滿城哀戚之色。
那千張信箋從承天門揮灑而下, 像是下了一場肅穆的雪。
三日後,魏軍再次兵臨楚地。
珺都城門大開,百姓列道跪迎,無一絲不忿。
亂世之中, 朝代更迭他們已經見過許多次, 誰當王, 誰稱霸, 於他們而言無甚分別。
魏洵就這樣不費一兵一卒,輕易奪得楚地,一統天下。
程錦上自願為保全一雙兒女,留在楚宮為質。
我出宮那日, 她來相送。
蹙眉問我:「一定要走嗎?王上對你的心意你不會看不出,又為何要……」
我搖搖頭, 示意她不必再說。
「我前半生已經吃盡了情愛之苦, 如今若是再一頭栽進去,那才叫蠢。」
嫁人不是看病, 頭疼醫頭, 腳疼醫腳。
大多是牽一發而動全身。
裴玄是個狼心狗肺的,未必就說明魏洵很好。
被裴玄丟下馬車的那一刻起,我就明白。
此生此世, 我都不會再將後背交給任何人。
她不再多話, 隻輕嘆一聲:「阿衡,惟願你此生,能平安順遂。」
我含笑點頭, 轉過身時。
一陣微風拂過,檐下風鈴清脆地響。
過往種種,都被吹進風裡。
廊角閃過一抹玄色。
我想。
應當是一隻銜草的雀鳥吧。
(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