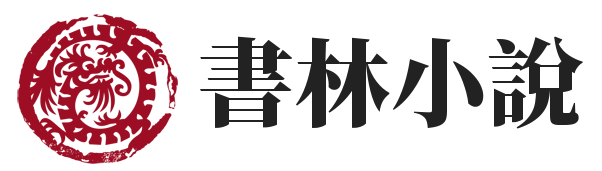第2章
他拉住我衣襟微微擺動,眼圈微紅,似是懇求:「想來不過比我多會些花樣……我也可以去學的……」
我用力推開他,轉身快步離去。
我絕不會心軟。
哥哥還在等著我。
晚上,他寫完文書後試探著叫我,我心下好奇一時沒理。
枕邊微陷,他小心地靠向我。
清朗的聲音一如流卿為人,沉靜純粹,低低地傳來:「我自知嘴拙,說不來甜言蜜語,人又呆板,不能察覺你的心思。」
他握住我的手:「我都會改,可不可以不要輕易就把我扔掉?」
我假裝無意識抽回手,彼此間的天塹哪裡能輕易翻越?
Advertisement
況且我哥哥……已經沒有時間了。
11
八月十五中秋,睿王府派人送來秋月宴請柬,司命出差。
我和流卿剛好落座在似姝公主對面。
溫柔嫻靜,雙眸翦水,真真是落落大方的可人兒,和流卿站一起誰都要說句天造地設的一對兒。
席間燈火輝煌,歌舞升平,一片鶯歌笑語。
忽地一個紅衣美男闖進來,正是我的新姘頭尹簫。
司命真的是職場老油條,寫的本子隨心所欲到可笑:青樓小倌大鬧王府宴會,並要求公主休了驸馬嫁給自己,公主贊其英勇,欣然接受……
他手指顫抖著指向我身邊的人:「我說你今日為何沒來看我,原是又被別的狐媚子勾去了?」
我糾正:「他是原配,你是小三。」
尹蕭冷笑:「不被愛的才是小三。」
我覺得這句話差不多就是「贊其英勇,欣然接受」的信號了。
於是眼裡擠出兩滴貓尿:「哇塞,突然就愛上勇敢的青樓小倌一枚了呀,本公主這就休了他。」
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,我站起來從袖子裡掏出司命準備好的休書,朝流卿臉上甩去。
他臉上被砸出一道紅印子,我忍住下意識想給他吹吹傷口的心思。
流卿萬年不變的冰山臉好生慌亂:「我知你心性稚嫩,這次……這次我就當沒聽見……下次休要再胡說了。」
我與尹簫十指相扣,來回晃悠:「你耳朵聽不見,眼睛總能看清吧?」
睿王從震驚中緩過勁兒,端起茶杯,用眼神朝似姝公主示意。
他一心想把似姝嫁給流卿,正愁找不著機會。
似姝公主紅唇輕啟:「流卿哥哥……溪禾姐姐真是太……」
流卿皺眉打斷,又朝睿王作揖:「勞煩似姝殿下不要用『姐姐真是太……不像我……』的句式起手,我娘子很好,我此生非她不可,先行告辭了。」
說完扯著我大步出門了。
餘光中,尹簫風中凌亂……
我幾次想甩開都沒成功,擺爛地被丟到馬車上。
12
睿王府到公主府不算近,我挑起窗簾看見月色分外皎潔。
氣氛僵持……
我咽了咽口水:「我……」
他捂住我的嘴,臉色煞白,像惡疾纏身:țú²「公主乖,現在月色多美,不若安靜欣賞會兒?」
我莫名羞惱,狠狠一口咬在他手心。
他現在應該看清我水性楊花的本性,然後和似姝公主相親相愛!
可惡的神仙,因為我卑微,因為我弱小,就可以隨便裝深情玩弄我嗎?
他任鮮血淋漓,若有所思,似有所感,抵著我的額頭:「你到底在害怕什麼?」
我知道自己無理取鬧,也不想解釋,面無表情地撕了一截衣袖給他包扎。
我裝作隨口闲聊:「你為什麼不給我畫像?」
他有些苦惱:「是我的疏忽,單知道你實際上不喜歡,但心理上需要。」
我故意把布條往緊了纏,看他疼得嘶氣:「你諷刺我附庸風雅是不是?那是因為……」
他挑眉,眼神疑惑。
我垂下眼眸,認輸般:「是因為是你畫的才想要。
「是因為想知道我在你眼裡究竟是什麼樣子——是不是有一點特殊?」
是因為或許從今以後都不會再相見,想留一些想念。
他神色黯然:「是我的錯。」
我哼了一聲:「你錯在哪?」
溫柔的月光盛在流卿眼睛裡,他把我的手按在心口,說得固執又認真:「錯在想得太少了,以為隻要把你畫在這裡就好了。」
呆子突然開竅了?
我臉上發燙,埋進他懷裡:「要給我畫得最漂亮,還有你說陪我買珠寶首飾,別忘了。」
他親在我軟軟的發頂,聲音像是心都酥了:「一直記在心裡,就等公主賞臉呢。」
我恨不得把自己嵌在他懷裡。
最後享受一刻吧。
13
久違的親密。
我從枕頭下摸出小刀,趴在他身上,靜靜看他沉睡的容顏。
做孩子時頑劣闖入魔族禁域,連爹娘都打算放棄了,是哥哥九S一生把我救出來的。
趴在他背上時眼前血紅一片,分不清到底是誰的血。
那麼好的哥哥,現在隻能躺在一張小小的床上,清醒的時間越來越短,好像明天就再也不能見到……我舍不得,我真的舍不得……
另一隻手輕輕從流卿眉骨處劃到嘴唇,好喜歡……連鼻梁上的小紅痣都喜歡。
不愛笑也不愛說話,下了床簡直是塊木頭;卻知道我最喜歡釵鳳鋪的首飾、最饞長月樓的蜜餞,上新了風雪夜也要買回來,但從不邀功,隻淡淡說一句娘子喜歡是最好。
其實……其實他也有點喜歡我吧?
可過了今天司命就回來了,我就沒機會下手了……
剔透的淚珠滴落到他臉上,刀劍不情不願地劃拉到心髒的位置:
恨我也好一劍了結也行,先讓我還了哥哥的命。
忽然一道冷光打掉我手中的刀,司命竟然提前回來了,他氣急敗壞地大叫:「你在幹什麼啊?」
流卿被驚醒,擋在我前面:「你是誰?怎麼三更半夜出現在我家?」
司命直跺腳:「我是誰不重要!你看見床上的刀了嗎?你枕邊人要S了你啊!還不快快從她身邊離開!」
「那也是我的家事,用不著你摻和。」流卿皺眉,怒視司命,「你憑什麼讓我從她身邊離開?那紙休書難道也是你的手筆?我娘子壓根不會寫字。」
簡直是亂七八糟、無理取鬧、毫無理由的指責。
我和司命都愣住了。
流卿喊來下人把司命以刺客之名五花大綁。
司命不好施展法術急得抓耳撓腮。
14
隻剩我們兩個人,氣氛無疑就變得窒息。
流卿臉色緊繃:「刀是怎麼回事?你隻要說,我就願意信。」
我低下頭:「就是想S了你。」
他閉了閉眼:「就為了那個人?今天在馬車上重歸於好都是假的?」
多說無益,我嗯了一聲。
像一條瀕S的魚最後的掙扎,他說得極為認真:「成婚時我們說過生S不棄,隻要你願意回頭,今晚就當什麼都沒發生。」
計劃反正失敗了。
不如讓他徹底恨上我,好投入似姝公主的懷抱。
也算助他歷劫一臂之力。
我摸起刀在他心口畫圈,接著拱火:「可是你我真的玩膩了……也許隻有S了你還有點意思。」
他面色無瀾,迎上劍鋒。
「好啊,S了我也是你的S鬼。
「我對你生生世世,永不罷休。」
心口猛地一顫,下意識松了手,他趁機拿出一截紅繩捆住我的手。
大眼瞪小眼。
沉默了很久。
他笑容極輕,像一捧易碎的浮冰:「我一遍一遍挽留你的樣子是不是很可笑?六公主在玩弄人心方面真是大師。」
他自嘲道:「從前我把公主當珍寶,深了淺了,輕了重了,你難受一下我都要內疚好幾天……
「但公主那麼愛偷吃,怎麼可能人人都像我那麼細致?想來公主其實是很隨便的人吧?」
紅燭熄滅。
一下一下又狠又兇。
疼……真的好疼……
15
京城風雲變幻,恐要變天。
流卿對外宣告我生了重病,將我軟禁起來。
我幾次三番逃跑失敗。
朝廷上下人心惶惶,自然沒人關注我這個廢物公主。
司命又不知從哪鑽出來。
「溪禾,能否ťū³再幫我一個忙?
「作為交換,我給你本古籍,那上面記載了換血重生的仙術,或許可以救你哥哥。」
聽到能救哥ẗũ₁哥,我條件反射般抬起頭。
況且即便當時刺S流卿成功,司命必定也會受到牽連,對他我還心懷愧疚。
我放下書卷:「您講吧。」
他一向堆滿笑容的臉上多了幾分憂愁:「你知道的,按照命書他本該和似姝公主攜手餘生。
「但是他拋舍不下你,違背了命書,未必能挨過天劫。」
我心被揪起,攥緊手心:「那,要我怎麼做?」
他附在我耳邊,一陣私語,掏出來一顆黑色丹藥。
我順從地接過,幹咽了下去。
16
下雪了,萬裡荒寒,天地間一片蒼涼的灰白。
我精神越來越差,吐血越來越頻繁。
總是睜不開眼睛,有時連動動手指都要費好大力氣。
本來在湖邊賞景,忽然身形一晃砸進了水裡。
冬天的湖水不必多說,我立馬發起高燒。
流卿頂著一身風雪進來,板著臉:「你又耍什麼花樣?」
司命的新計劃徐徐進行,我再犟下去也沒意思。
於是朝他招招手:「咳咳……相公過來。」
他遲疑了一下,坐在我床邊。
我乖順地靠著,感覺背後的胸膛緊繃繃的,好不自在似的。
心下覺得好笑,我打趣道:「你別扭什麼?你晚上不是挺能放得開嗎?」
流卿眉頭緊皺,仍然有所提防。
我也不惱,把手塞進他掌心,自顧自地說話:「你最近很少來看我,我其實很想你。」
這是真的。
我常常夢回我們大婚的時候。
蓋頭被撩開後,抬眼看見流卿驚豔絕倫的臉。
想他從前真的好溫柔……
眼前的流卿垂下眼眸,神色冷淡:「撒嬌也沒用,我不會再被你騙了。」
屋外蒼白的光勾勒出他薄涼的輪廓,現實和回憶的巨大落差,讓我又委屈又傷心:「對不起……對不起,但我不想的。」
他歪著頭,笑得惡意十足:「你不想的?哪件事是你不想的?人盡可夫?還是準備為了奸夫S了我?
「六公主,你真的是很虛偽的人。」
他把我推到床上,幽怨得像多年不曾投胎的惡鬼:「我真倒霉啊,喜歡上你這麼一個爛人。」
我斷斷續續哭著求饒:「疼……好疼,相公,親親我。」
一隻大手控著力掐住我的脖子:「誰是你相公?有沒有叫過別人?」
我連連搖頭:「流卿是相公,隻有流卿……」
他不情不願地在我唇上啄了一下,惡狠狠道:「下次不準撒嬌。一心軟,你就不知道又要去勾引誰。」
我主動纏住他的唇舌:「隻勾引你。」
手環住他堅實的腰間,忽然嗓子好痒好痒,咳出來一大攤血,褥子幾乎全染紅了。
暈厥前隻聽見流卿顫抖地叫我,恍惚間好像又看見了以前那個不愛說話,但事事依著我的少年。
17
京城名醫輪流來看診,皆是搖頭嘆息,查不出病因。
司命化作仙風道骨的雲遊半仙,謊稱途經這府邸見黑雲一片,猜測有人大限將至。
僕人欣喜地把高人迎到我床前,他飛快地和我對視一眼,假裝把脈:「夫人並非病在身體,而是……」
流卿揮手:「直說無妨。」
司命斟酌用詞:「是由於……二位大人氣場不和,強結姻緣,勢必有傷。」
流卿一言不發,面色不豫地盯著他,良久後才冷笑著嗆聲:「什麼庸醫。」
司命彎腰作揖:「大人,您若不信,大可等到三天後……到時候夫人必定……暴斃。」
琉璃玉盞噼裡啪啦碎了一地,流卿利劍出鞘,直指司命:「敢再胡說,我S了你。」
司命不卑不亢道:「您可以等到三天後看看是否如我所說。」
沉默。
良久的沉默。
……
一道淚痕滑過,流卿聲音發苦:「我放她走,她就會ţů⁷好起來,是嗎?」
司命扭過頭,似是不忍:「回大人,是的,而且隻有這種方法。」
夜裡。
一輛馬車緩緩停在偏門處。
我受不住風寒,又咳了兩聲。
流卿手攥緊又放松,像是終有不甘:「你走吧。」
往後估計見不著面了,我想拿回我的妖丹,於是說:「流卿,最後親親我吧。」
他陰冷一笑,鉗住我的下巴,迫使我和他對視:
「你有很重要的東西放在我身上吧?
「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什麼,也不知道你到底要去哪。